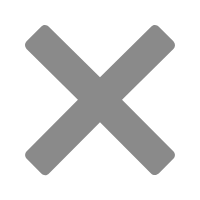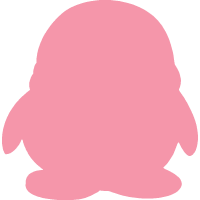3.石塔
石头溪两侧的树木密集,沉静的榆树,妩媚的枫树,平凡的橡树,古老的山楂树,还有大片大片的松柏和乔木。小溪流里只有在下雨的时候会注满水,平时是一条条干枯的石滩,里面满是被汛期冲刷得圆润光滑的大大小小的石头,每一个石头好像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有着自己的颜色和纹路,静静地等待着世间的因缘际会。
过去我跟着阿爸在河道里捡石头,他搬大的,我搬小的,然后我们把大大小小的石头叠放在一起,看谁的石塔磊得高。很多石头棱角不平,并不是上佳之选,所以游戏的关键就是保持耐心和细节,先找到最平滑光顺的石头,由大到小一层叠着一层的往上摞,越到后来越需要稳健,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阿爸往往可以心平气和的一搭就是一天,让大大小小的石头通天塔一样的高高叠起来构成也幢幢造型各异的石头塔,有的石塔是孤零零的一个,有的是围成一圈,或是连成一排的石塔阵,具体的形状完全是凭当时的条件而定,每一个石塔和石阵也都没有重样的。我那时年纪小贪快好强,毛毛躁躁的常常功亏一篑,搭得快,倒得更快,自己搭的石塔只有阿爸那些的一半高,更不用说我常常一不小心就把石塔搭歪了。
有的时候我故意淘气跑到阿爸搭好的石塔边,冷不丁的用手一推,就把阿爸辛苦了大半天的石塔推倒。阿爸从来都不生气,总是呵呵一笑,如果有时间就重新再搭一座,如果天色晚了,就过几天再来。阿爸说这是修行的基本功,叫做堆石,练的就是定力和耐心。
一整天我都在堆石,看似枯燥的堆石,却最能磨砺人的性情。煦暖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在溪流间闪现着斑驳的光芒,石滩中间涓涓流淌的溪水是高山上雪水融化后汇集而成,清澈透明的水流越过浅石,哗啦啦地流淌过午后的山地。我堆石累了,就脱下鞋子,溪水凉嗖嗖地,刚刚覆盖过脚面,顺流而下的落叶和树枝绕过我的脚踝,让我觉得有些痒痒的。
我坐了一会儿觉得休息得差不多了,起身在石头溪里走来走去,一边寻找着合适的石块,石头最好是扁平的,如果不是扁平也要是能嵌在一起的形状,由大到小,层次递进。后来我琢磨着堆石也不一定只是一柱擎天,也可以从两边开始,最后慢慢倾斜做成一个拱门的样子。
时间好像看不见的河流穿过河床,当暮色来临,溪旁巨大的岩石上已经搭建起好几座我自己的石塔,橘色的夕阳在高高的树尖熠熠生辉,几缕阳光穿透繁茂的枝叶直勾勾地滴落在石塔上,一座座石塔好像活了过来,每一个侧面都反射出光泽,恍如冥冥中有种力量在指引着,一种神秘的辉煌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真让我着迷,阿爸说天地间无处不是这样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可能是一缕阳光,可能是一颗雨滴,可能是一个笑容,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次邂逅,可能是一次碰撞,神秘莫测的缘分将时间万物连接在一起,不可琢磨地在世间辗转磨砺,最后却往往能成就了一种摄人心魂的庄严。
心中的悲伤在不疾不徐的堆石中缓解了许多,我好像能感觉到阿爸陪伴我时那种安稳平静的心情。童年的记忆如同无数透明的小鱼将我团团围住,溪边的空地上响起了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
记得那时山里的孩子们看见我和阿爸玩堆石,慢慢聚拢过来观看,阿爸正愁我没有玩伴,便让我和他们比赛堆石,后来除了堆石阿爸也教他们在沙地上写字画画,一回生二回熟,就这样我有了童年的一群小伙伴。虞山,小蛮,阿云,大眼小眼兄弟俩儿,都是一起玩大的朋友,还有漠笛。
虞山是孩子王,从小个子就很大,他喜欢爬上巨石,从高处跳下,或是在林间的空地上奔跑。在他眼里,山里所有的石头都是用来跳的,从一块发白的石头跳到另一块颜色暗沉的石头;所有的树都是用来爬的,无论是山野中的,溪边的或是院子里的,虞山都可以顺着树枝爬上去,然后掏鸟蛋,又或者是摘蜂巢;所有的溪流都是用来涉水的。有的时候他指挥我们脱掉鞋子涉水而行。光脚踩在水底下的鹅卵石上容易打滑,我们就拄着树枝当拐杖,有了小伙伴们石头溪边永远都是朗朗的欢笑声。
漠笛也会来看我们游戏,但他总是离得远远地,或者坐在树枝上,或者站在灌木后隔着老远往这边看,和我们所有人都保持着距离。漠笛不是山里人,高鼻梁,皮肤白皙,样貌文静清秀得像个女孩子。他性格内向沉默,和山里孩子的爽朗颇不相同,女孩们对他十二分好奇,男孩子们则莫名其妙地瞧不起他,有时甚至是故意找茬。关于漠笛的身世,说法很多,其中一个说法是他从小有自闭症被父母遗弃,后来被送到了山里跟爷爷住,爷爷病死了,最后就剩下漠笛自己靠着采山里的果子和卖采药为生。漠笛左手有一个併指,这成为了孩子们嫌弃他的又一个理由,不知是谁送给了漠笛一个外号叫“六指怪”,漠笛听了脸色阴沉更加不愿意和大家在一起玩了。
山里的孩子们越是喜欢欺负捉弄漠笛,他就越是倔强,好几次不顾死活以一人之力对抗一大群孩子,哪怕打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后来孩子们见他蛮横,便干脆孤立他,见到漠笛大家好像瘟疫一般,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漠笛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也从来不往孩子堆里凑。
平时阿爸阿妈都教导我要善待他人,那是我看见孩子们孤立漠笛,隐隐感觉到这样对待一个人是不对的。一次我们玩打仗的游戏,这边一大群孩子,而对手只有一个就是那边芦草里的漠笛。看见他腹背受敌的样子,我觉得这不公平,自愿当漠笛的帮手,战斗的规则很简单,如果被炮弹打中脸部,头部和身体,你就得倒下“死掉”。我帮着漠笛准备泥球弹药,他则负责攻打。战斗的双方用拳头大的泥球相互投掷。打到胳膊或是大腿就要倒下,算受伤。“伤员”们必须静静地躺着数完一百,数完了就可以起来继续战斗。这样的战斗没有赢家。玩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游戏在争吵与叫骂中解散了。我和漠笛在河里尽量把手上脚上衣服上的泥土洗干净。漠笛一路把我送回家,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说。
然而第二天,我们的同盟就瓦解了。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我听见男孩子们拍着手大叫“青楹喜欢上六指怪啦”“青楹要给漠笛当老婆啦!” 大家都指着我笑做一团。小蛮是和我玩得最要好的结拜姐妹,也拍手笑着大声传唱这些话。
我又气又急大喊你们乱说,孩子反而笑得更开心了。虞山本来也在笑,看我真的急得掉眼泪了,连忙出来为我说话,他威胁说谁如果再敢瞎喊,就等着挨打。果然小眼刚要说怪话,就被虞山抓住衣领打了两拳。男孩子们都住了嘴,可是看我的眼神依旧是坏坏的笑意,这种玩笑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近乎侮辱。
漠笛这时正好迎面走过来,他看见我露出欢喜的表情,没有跟过去一样避开,而是停下脚步一幅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当时满心的气恼无处发泄,耳边依旧是孩子们嘻嘻哈哈的笑声。老远看见漠笛,好像一切的委屈都有了目标,泪痕未干的我用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对着漠笛大喊道,你这个讨厌的六指怪,以后离我远点!
漠笛的眼中瞬间充斥了震惊和失望,那种受伤的表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但是他很快地恢复了平日的冷漠。他快速移开了视线不再看我,一言不发地转身往树林后面走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林子深处。我的心猛地一震,一种愧疚之情油然而生,那感觉就好象是面前有一只流血的小兽,我走上前去假装要为他疗伤,结果却又更凶残地插了他一刀。
之后好几年,我和漠笛没有了任何的交往,好像彼此在回避对方,阿妈做了好吃的食物,我带给朋友们吃,大家都会围过来抢着要,唯独漠笛目不斜视地走开,冷着脸一副谁都不理的样子。
在我心中,阿妈和阿爸的感情极好,他们是天下最般配最关爱的夫妻,我原本应该喜欢像阿爸那样让我感到温暖可靠的男人才对,可我偏偏对忽冷忽热的漠笛情有独钟,可见天下的情爱并不只是因为喜乐而存在的,有的时候反而是越痛越爱,如我这般只怕要用痴顽两字才能形容。
如今,孤儿般的自己正仰望着夜空,思念一个永远不能相守相伴的人,还有比这更傻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