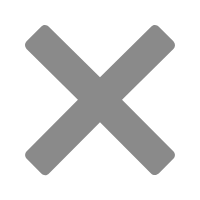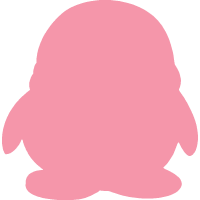第5章:只是领了结婚证的陌生男人
“陈律师!”
“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更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担保,我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件事情打来电话了,也不要去打扰我姐姐!”
“星子!你不出面担保可以!但你和你姐必须要给钱!二十万!”
电话里突然传出老头儿的声音。
她身体应激反应,一股寒意直涌上来。
“陈律师?”
她警惕地叫了一声。
“细妹,俺告诉恁俩,恁给俺儿做担保人,当初恁报警抓俺儿这事就过去了。否则俺跟恁俩没完!”
这次是个老婆子的声音。
虽然过去了六年,但这两个声音她一点没忘,深深烙印在她潜意识内。
无疑,倪家俩老正在和陈律师在一起。
她气到失语,好一会才找回声音。
恶狠狠地怼道:“倪大寿蹲监狱,那是他罪有应得!”
倪添禄夺过手机气呼呼地大叫:“住口!妳们姐俩身上流着的是倪家的血!”
“这几年妳们没有尽到半点赡养的义务!我儿子被妳们送进去了,而妳们姐俩,一个嫁城里人,有车又有房,一个上了名牌大学,稳稳站住了脚跟!现在我儿子病了,我要给我儿子治病!妳们姐妹拿钱出来弥补,这个天经地义!”
倪老太则在一旁煽风点火。
“给她说,还要给俺们养老!”
“对!”
见老伴儿话说不到重点,她又抢过电话。
“恁现在过来接俺们,俺们现在陈律师的事务所,要是今天过不来,明天就到南二里,第五看守所对面的如家旅馆接俺们!”
“还有,记得多带点钱,给俺们付了住宿的费用!”
“老婆子,你和她说让溪子把家里的房间拾掇拾掇,咱们就住在溪子家。”
彩星辰气得浑身哆嗦。
“做梦!”
她重重地说到,然后挂断电话。
站在人声嘈杂的校门口,只有她一个人的世界是无声的。
回了趟姐姐家,姐夫并不在家,说是在公司加班。
发现姐姐不是因为接到陈律师的电话才叫她回来,她松了口气。
姐姐说想出去做事,看中几个工作岗位,让她帮拿拿主意,其二是想把女儿转到她学校附近的幼儿园,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让她帮忙接一下。
彩星辰觉得可行,就答应了下来。
临走时,她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和姐姐说了倪大寿的事。
彩星溪气得破口大骂,说他死了没人收尸也不会多看他一眼。她恨透了倪大寿。
倪大寿是村里出了名的泼皮户,他的父母,也就是她的爷爷奶奶更是为虎作伥的老混物。
当年,十八岁的母亲陪表姐走亲,被她爷爷奶奶看上,于是集结了村里几个壮汉,抢了亲,强行将人留下。
倪大寿是个奸懒馋滑的烂赌鬼,将人糟践生下孩子之后,又把母亲转手给了村里的几个老光棍生子,赚取所谓的“生子费”。
当年那些个老光棍上门讨价还价的时候,她就在一旁看着,生儿子八百,女儿三百,怀上没生出来,不幸夭折就算他倪大寿的,人送回来就行。
母亲辗转几家,送回来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就这样倪大寿还不放过她,又强迫她怀孕。
倪家人怕她发病伤着肚子里的“儿子”,就拿狗链子拴住她脖子,关在笼子里。
是村长用土方子给她治疗,才稍微改善了些,清醒的时候只认得两个女儿,但发起病就抓着菜刀见人砍人。
后来一次倪大寿又赌大了,想故技重施,不过,这次他将主意打到了十几岁的姐姐头上。
母亲大受刺激,阻拦时抓伤倪大寿的眼睛,倪大寿这个丧心病狂的,抓起农机柴油桶就往妻子头上泼,接着一把火引燃。
听到姐姐愤慨的大骂,坚称绝对不会给这人渣做任何担保,她才放心离开。
连续三天她都能接到倪添禄用不同的号码打来,电话里威胁她不出现就闹到她学校去,去姐姐小区楼下拉横幅,广而告之她们姊妹俩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闹到她姐夫的单位去,让他们日后没法见人。
彩星辰担心姐姐和外甥女的安危,让姐姐换了电话号码,又吩咐她出门带上辣椒水,以免遇到倪添禄带人来闹事,没有防备。
拖着疲惫的心情拧开门把,就看到一抹颀长的身影在背对着她打电话。
他回来了吗?
她以为他出差要去一周,没想到才三天就回来了。
“去哪了?这么晚才回来。”
听到动静,阎隐白结束通话。
“去我姐那里了,阎先生需要我帮忙铺床吗?”
“你会吗?”
阎隐白看着她略显稚嫩的脸。
“嗯。会。”
“跟我来。”
他表情漠然地转身走向主卧,彩星辰尾随而入,见他静立一旁看着,仿佛一个考官。
彩星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就好比参加高考,可明明她只是来帮忙的。
了解他是个不好相与的讲究人,,她脱下外套,然后掏出随身携带的消毒喷雾,把自己全身上下喷了一遍,才动手去扯褥子。
指尖触及的被子异常亲肤,似玫瑰花瓣,柔软无比。
这令她想起了影视圈某女星离婚后再婚,都不舍得丢弃与前任的两百万床垫。连日来的那种精神紧绷感在这一刻松懈下来,她好想就这么躺进去。
铺好被褥,转身时,她留意到主卧里还放着三只黑色行李箱。
“床已经铺好了,我替您把衣服都挂起来。”
她对他笑了笑,习惯性地要去收拾,指尖刚碰到行李箱的拉杆,沁心凉的声音就冻透了她的手。
“等等。”
“怎……怎么了吗?”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可随便打开我的物品,记住了。”
彩星辰心里咯噔一下,顿时醒悟。
虽然他们之间领了证,他也说过会和自己培养感情,但终究是相识不久,彼此之间还是陌生人的状态。
“噢。那我出去了。”
她悻悻然抬脚。
“稍等。”
“阎先生还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