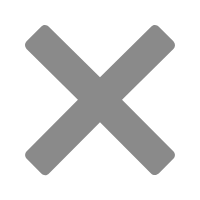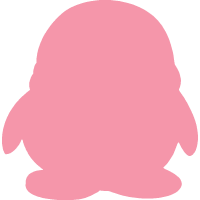第一百四十八章 审问
江倚澜的伤恢复的很快,早在几年前,她就研发出了一种药物,可以快速愈合外伤伤口,并且不会留疤。
但是脚腕上的伤拖了将近一天才治疗,现在脚踝处还有一道淡粉色的痕迹。
这件事情最终还是惊动了联盟,有人指认这个人就是江倚澜,虽然她做成了一桩好事,却还要因为这件事走一趟联邦法庭。
那天江倚澜刚刚踏出校门拐过第一个十字路口,两列防爆警察持着盾在她身前挡出了一条有些通道,紧接着,一窝蜂的记者蜂拥而至。
江倚澜瞥了一眼她们胸前的记者证,还是军事准入。
无非是问一些什么英雄问题。
“江女士,请问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怎么这么准确的进入了敌方的据点?”
“江女士,现在外界有很多你的支持者,希望你能说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
“江女士,能否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江倚澜面前的道路被记者们挤得越来越窄,他们争先恐后地提问着生怕自己错过江倚澜说的每一个字。
只有江倚澜是人群里最淡然的一个人,甚至还能抽出一只手拨开那个快要怼到自己脸上的镜头。
大白天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开闪光灯,江倚澜突然停住脚步弯下了腰,所有人的心情跟着她的动作颤了一下。
旁边警卫也攥紧了手里的武器,她又不是恐怖分子,怎么看她的眼神这么恐惧?
只是一秒钟,江倚澜直起来身子,又悠闲的往前走去,只是手里多了一枚小石子,在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江倚澜微曲自己修长且白皙的手指用力一弹,碎了前方一个正在亮起的闪光灯。
这件事情已经在媒体上播报了,很多人都在义愤填膺,同时也在夸奖着那个只身一人深入敌方腹地的江倚澜。
只是她们不知道这个人还要去联邦法庭走一遭。
江倚澜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她只是气定神闲的走着,穿过那片由她根本没看清一张的人脸与闪光灯声构成的路。
身后有两名军官催促着,趁那名被打碎闪光灯的记者没反应过来之前,江倚澜冲他微笑了一下,转身跨上了押送车。
车门关上的时候,她似乎听到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不愧是联邦政府,押送她都用了好大的阵仗,上车之前她往车后方看了一眼,至少有八台防弹防爆的装甲车。
江倚澜所在的车厢内有三名押送的人,有两名比较年轻的坐在最前面,还有一位看起来官职比较大的坐在她身边。
冲锋枪一直在他们手中紧握着不敢放松,他们紧紧的盯着江倚澜,生怕有什么闪失。
江倚澜觉得押送车程有些无聊,她先闭目小憩了一会儿。
车辆开始逐渐颠簸了起来,晃得她有些难受,她睁开眼睛,刚好和前面一个年轻人对上了眼神。
瞬间,年轻人的唇角紧抿起来,模样如临大敌。
江倚澜的嘴角勾起一丝淡然的微笑,“你是在害怕我吗?”
年轻人的身体绷得更紧了,攥着枪的手上因为用力而爆起了青筋,如果江倚澜理他再近一点,就可以看到有汗滴在他的额角滑落。
没等年轻人回答,江倚澜身边的中年男子语气严肃的开口了,他低声警告道:“禁止交流。”
年轻人听到后,立刻扭头转向车厢口。
江倚澜无所谓的再次闭上眼睛,她的背后是铁丝网,随着车厢的晃动发出清脆的声响,现在似乎正在爬坡,油门声猛而闷。
大概还有二十分钟?
脑海里计算了一下路程,江倚澜晃了晃被手铐紧紧铐住的手。
可是这手铐的质量不怎么好啊。
不过无所谓,她也没想逃,正好去那里会会自己的老伙计,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
审问江倚澜的临时联邦军事法庭位于一座山腰的密林中,这些建筑总爱设计到一些鸟不
拉屎的地方,大约会有好几个小时车程,在郊外,还需要跨过一个绵长的峡谷。
押送的过程都没有出什么差错,顺畅的让人觉得不现实。
行程过了一多半,正当所有人的戒备都放松了一些,甚至有一个年轻军官打了两个哈欠。
接着,他们的头顶传来一声巨响,江倚澜觉得自己耳朵有些震的慌。
是重型装甲车在快速前行的时候紧急刹停的声音,制动片摩擦产生的尖啸声响彻整个山谷。
四人因惯性向前冲去,江倚澜手还铐着,肩膀在车内钢壁上狠撞了一记,发出一声闷响
押送官们瞬间清醒过来,他们反应极快,迅速的将自己身形稳住,江倚澜身边的军官立刻掏出腰间的手枪,用力顶住她的腰:“别动,老实一点儿!”
那两个年轻人则端起枪背靠着背,姿势非常的谨慎。
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着,他们注意听着外面的声音。
顷刻之间,外面传来树叶声被穿透摩擦的奇怪声音,又过了几秒种,外面似乎传来了直升机的螺旋桨打在树干和山边岩石上的愚钝摩擦过的声音,那声音有力的穿透了押送装甲车震颤着的钢板,径直钻入车内军官和江倚澜的耳朵里。
一声又一声的撞击声短暂而又急促地响着,令人毛骨悚然。
军官们一个个面色惨白,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上级说了,不能让这个女人受伤,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安全的把她送到联邦法庭。
听着外面的打斗声,江倚澜并无惧意,并且心中腾升起一股玩味的意思。
这种简单粗暴的做事风格、一点儿都不合时宜的解救时机,现在在外面的究竟是谁,这个方式,不像是军事基地人的作风。
车被人拦下停在了原地,刚刚剧烈的打斗声瞬间全部消失了,只剩下了山谷的风呼啸着划过车厢的声音。
车里的每个人都不敢出声音,只是每个人的表情大有不同。
前面一个年轻长官刚要开口为什么,车厢的一侧颠簸着向一边移了过去,似乎是被铲到了某个地方,接着,失重的感觉刺激了每个人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