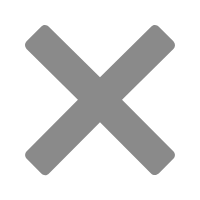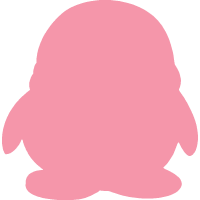第1卷第八十七章葛神异闻录之纯真年代87
孔慧:
赠葛亦民:
我们其实已经分手了,因为两年来,我没看见过你,你也未看见过我(在感情上、思想上)。
然而,这是事实,一本精致的缎面本子放在我面前,这么多同学的话语响在我身边(虽然不是对我说的),一切又勾起了我那早已沉寂下来了的情愫。
唉!罢!罢!罢!何必谈这些伤怀的事呢?我这是在给我的老同学写临别赠言啊!向一个虽已相识,但互不了解的同学说这道那,这能表明我是个什么人呢?还是让我饱满精神,向我们这位才华横溢的同学祝福几句吧!可是我知道,葛亦民,你一定是不屑于那平庸的,应付差使性质的话语的,于是只有仔细地想想,搜尽我那可怜的资本,写一句发自肺腑的心愿吧!
请在白洁的纸上绘一幅蒙娜丽莎吧!中国的!
谈不上朋友的学友:孔慧
句容县三岔中学。
何宪梅;
赠学友:
你是无畏的海燕,在搏击,在飞翔,愿你在知识的海洋里永远寻珠探宝。祝你展翅蓝天,翱翔万里!
学友:何宪梅
黄晓敏:
与君同窗共读两春秋,但对君的了解却很少。在这分手之际,只能用寸管表达我对君的看法:
潇洒英俊
才华横溢
谈吐风雅
胸怀大志
乐于助人
可敬不可亲
愿分别能使我们培植友情!
愿君人生得志!
学友:黄晓敏
王锋:
老亦民:
我一直是这么称呼你的,现在我仍这么称呼你。
(老亦民),我为别人写的留言总是很快的,然而拿到你的留言簿子时,我止了又止,改了又改,为此,还撕了你一张纸,我总觉得我要讲的话很多,要对你讲的话很多!
老亦民,记得吗?高一开学第一天,你的床在我对面上层。记得那是一个大热天,你来得早,床已铺好了。我热得直冒汗,看见你床上有把扇子,便向上借了用用。由于我怕你听不懂茅山土话,特地用普通话讲,可是你把普通话中的“扇”的读音误以为大卓土话“上”,结果,你以为我要上你床,于是往床里挪了挪,叫我上来。
这件事,事后我曾不止一次地对你讲起,而且,每讲一遍,我都要“骂”你一遍,笑你听不懂普通话,你不争辩,只是咧着嘴笑,那神气劲儿,想起叫人忍俊不禁。我写到这儿,也笑出声,致使邻桌们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老亦民,记得吗?到了不冷不热的天气了,每天晚自习课后,回到宿舍,我急急忙忙洗了脚,就爬上你的床,开始了每天十五分钟的谈天说地节目。谈话中,我一次又一次问你累不累,困不困,你总是说:“困什么?”因此,我们的十五分钟谈天说地经常延长好长时间。我们谈话内容也很广,诗词,国外名人,班上同学性格以及一些看不惯眼的人。可笑的是,我们经常同时看不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原因呢?说不清,反正看不惯。
老亦民,那时你的床靠着窗子。每当月儿圆时,月光隔了窗照了进来,照到你的床上,我们头并头,紧挨着躺着,各自谈着心中最宝贵的东西,常常一直谈到同宿舍的人响起了鼾声。
老亦民,(我那时对你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我一次又一次要求你重复你爷爷的事情,你也一次又一次津津有味地对我讲着你太爷的故事。那时你还很小,你的太爷便叫你背词诗。当你告诉我,你坐在太爷腿上恳求他再讲一个故事时,我的心便激动起来,我仿佛与你共同回到了儿时,而每当此时,我便看到你两眼充满感情地望着月儿,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老亦民,有人说你无情,我要说,那是他不了解你,其实,你的感情很充沛,而且表现的很分别,也许这只我一人知道吧!
老亦民,我曾对你说:“在我存在的十七年(高一时),你也存在。”你便笑着说:“当然”,然而我又说:“假如我们其中有一个没考中县中,那我们不就不相识吗?”你又笑着说:“事情就这么巧”,我终于无话可说了。
老亦民,我曾不止一次地笑你眼窝深,就象班上张贴的达尔文的画像。我也时常叫你鼓起手臂肌肉,让我捏着玩。你总是答应了。也许这就是他们说你的姑娘性格。
于是,我的私心得到了满足,我发现,除了我,还没人真正了解你,至少目前为止。
老亦民,还记得这么一个动作吗?在身上抓一抓,然后放在鼻前闻一闻。我问你闻什么,你总是说这是不自觉地,其实也没闻,但不闻又觉得可惜了。
终于,到了高一学期结束,我们要分科了,我不只一次地请求你和我一道学理科,但你一次又一次劝服了我,说即使我们不在一班,我们也会有许多联系的。的确,我们高二高三一直保持联系。
现在我们就要分手了,分手时,我也没什么华丽词藻赠给你,因为我知道,华丽词藻中听但不中用。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而且我们在前进过程中不会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会不时遇到困难。至于当作家,伟人,那还是奋斗以后的事,亦民!理解我吗?
老亦民,答应我一个小小请求吧,当你发表第一篇文章时,来信告诉我,让我也为你高兴。
友:黑子。
草于 86.3.28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