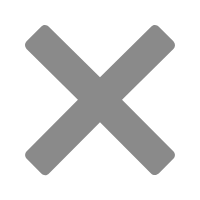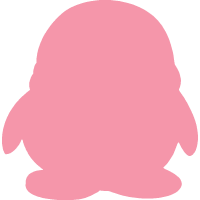第十四章 只要你让我活着
竟是将她白送到这南馆中,任人玩弄!
白流霜咬牙切齿,眼中寒意浓重,一双清亮的眸子愤恨的瞪着将她团团围住的一众丑陋的嘴脸。
暗暗握起拳头,却发觉自己竟浑身无力,想来是来时的路上被君洵钰的属下灌了软筋散。
冷静,她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要活着!
这是白流霜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哐当’一声,一把银晃晃的短匕扔在了白流霜的面前,她缓缓抬头,这才看见在二楼的雅座上,君洵钰正居高临下的看着。
修长的手指捏着白玉杯,性感的薄唇浅尝慢啄的品尝着杯中茗茶,如世上最优雅的绅士,风度翩翩,矝贵如厮。
见白流霜望了过来,君洵钰挑了挑眉,嘴角勾出一个悦愉的弧度,似乎心情不错:“给个机会你,杀了他们,全身而退!”
白流霜认得那把匕首,正是四年前,她杀君洵钰一行三人的那一把。
匕首极为锋利,刀柄刻着繁复的图案,一看便知是出自官家贵胄之物。
她缓缓伸手,用尽全身力气将那匕首攥在手心,冰冷的目光一一环视面前丑陋的嘴脸,匕首还未曾挥出去,便被人轻易的捏住了手腕。
再一次‘哐’的一声掷了出去。
头发被一双油腻的大手重重一扯,她整个人便狼狈的趴在了地上,周遭一阵哄堂大笑。
近乎无力的姿态,让白流霜在这异世第一次想到了死,可是,梓墨苍白的脸庞闯进脑海,她答应过他,一定会治好他的病,然后带着他游山玩水,让他做一个正常的孩子。
她不能倒下。
这个支撑着她活下去的信念,让白流霜似乎重新有了力气,在一众讥讽的目光中,她艰难的、缓慢的爬了起来。
身上无力,脚下虚浮,可她却仍旧将背脊挺的笔直,目光望向二楼那穿着锦衣华服、高贵如厮的男人,嘴角勾起了一丝近乎诡异的浅笑。
“你想让我做什么,不用下药,直接说,我定然照办,只要你让我活着!”
君洵钰的眸子眯了眯,握着杯盏的手微微一紧,四年了,他确实已经忘了她的模样,可他却清楚的记得自己昏迷前这个女人那近乎诡异的一笑。
与此时她嘴边的笑意如出一辙。
他略略惊讶,似乎有些想象不出,是多么强大的灵魂,才能使一个人在这种近乎地狱的环境里,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并积极与他谈条件。
见君洵钰不说话,白流霜干脆主动出击,她踉踉跄跄的走到临近的一桌,随手拿了一壶酒,仰起脖子,将壶口对准自己的嘴,猛灌了下去。
看的出来,她并不是个中高手,一壶酒下肚,白流霜的脸色已是绯红,醉眼迷离之下,更是显得她媚惑似妖。
伸手,搭上面前的男人:“谁先来?”
手指一一划过那一张张垂涎三尺的嘴脸,既然躲不过,她便取其最轻,只要她活着,梓墨才有救治的希望。
被勾住的男子立马喜笑颜开,揽着白流霜便要抱进房,便在这时,向卿急步而来,附在君洵钰的耳边说了几句,便见君洵钰‘腾’的起身,冷脸离去。
“来人,将此人押入府中!”一声令下,白流霜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强撑着的身子不受控制的往下滑,终昏死了过去。
……
上平县季家
白流霜离开已有三日了,这里离京城不足百里,便是好几个来回,也已经足够了。
季枫坐立难安,终于还是拗不过心里的担心,简单的收拾了一番,便要偷偷上京城去找白流霜。
“枫儿,你看看,这信上写的是什么?”
季枫还未来得及出门,便被季母唤了过去,季家亲戚极少,自打季父过世后,家中亲戚几乎不再往来,因此也显少有人给季家寄信件。
他讶异的接过书信,便见几行绢秀的小字。
“是流霜写来的!”季枫欣喜的念着书信,一颗悬着的心,也跟着这封书信落地了,良久,他才咧唇一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看向季母:“娘,我去衙门了!”
说罢,季枫便悄悄的回房,将收拾好的包袱又重新放了回去,心情愉悦的出了门。
他前脚刚走,季母便叹息了起来,嘴里喃喃道:“枫儿,你可别怪娘,往后你就会懂为娘的苦心了!”
这封信并不是白流霜托人寄来的,而是白流霜临行前交给她的,白流霜早就料到季枫会去京城找她,因此,留下了三封书信,每隔数日,便让季母取出一封。
除此之外,白流霜还将这次擒拿采花大盗的赏金全数给了她,数百两银子,够白梓墨近日的诊金,她安排的妥妥当当。
生怕有一丝一毫的连累季家。
想到这里,季母的眼眶微微湿润,唇瓣嚅动,再次叹息一声:“可怜的孩子,你让季大娘心里如何过得去?”
“婆婆,你怎么哭了?”
也不知何时,睡着的白梓墨已然转醒,他睁着一对如黑葡萄般深遂的双眼看着季母,不解的问道。
说罢,强行爬起身,小心翼翼的为季母拭去眼角的泪珠子。
季母一听,心里更是百感交集,一把抱住白梓墨:“梓墨,你放心,婆婆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白梓墨不懂,却还是乖顺的点了点头:“婆婆别哭,我娘说了,她过几日便回来了,界时,便让娘给婆婆买好吃的,可好?”
季母破涕为笑,心里却是越发的心疼这个孩子。